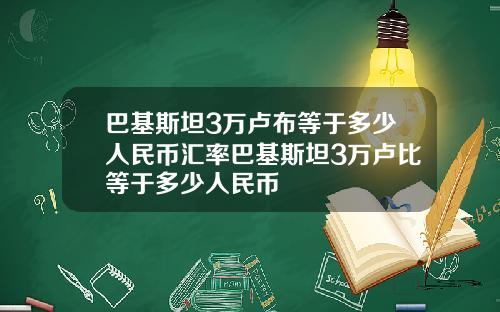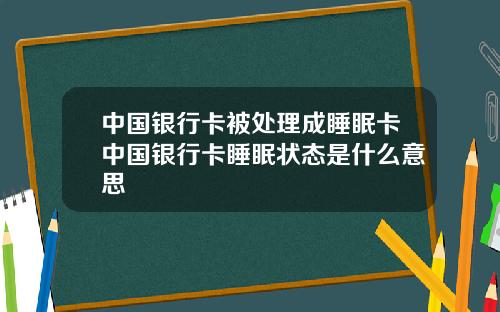作者:Eric Hynes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Reverse Shot》(2004年12月10日)
俗话说得好:离别不会使我们的心变得更深情——离别只会使它在被窝里爬来爬去,呜咽着,不停地悸动着,睡不着觉,度日如年,变得不再温情了,再也没有像温情那般轻柔的存在了,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心痛。因为受伤而心痛,因为愤怒而心痛,因为被扔下或不得不离开而心痛,因为所有那些不间断的感觉而心痛。
蔡明亮的作品无比微妙而有机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但在《你那边几点》中,他探索了「离开」这个词的每一层有价值的内涵,从外出旅行到最后的鞠躬;从做出实质性的个人改变到简单地说声再见。更妙的是,他表明了这一切都是一样的痛苦。
《你那边几点》
片名所提出的熟悉的、看似轻松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恰如其分的、通俗的表达,不仅仅是某种存在状态。时间,不是一个固定的事实,而是一个串谋的构造,一个结构——同时非常有用和必要——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
蔡明亮把时间拉回到它最初的隐喻层面,在那里它滴答作响,铁皮人的崭新的一颗心填补了原来的空白,尽其所能地理解我们背后的、面前的,以及超越我们自身的存在。
由于太慢、太沮丧,我们无法在瞬间的此时此地进行操作,但正如这个问题所暗示的那样,我们仍然能够想象(或至少是想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能够胡乱地将心放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方。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空间维度,也给我们带来心碎。
第一个场景原本平淡无奇,一个老人(苗天 饰)安静地坐在空荡荡的公寓里,或者走来走去,这确立了影片的语汇(固定机位的深焦长镜头),定下了基调(安静、专注、怪诞的),并立即让观众参与到对缺席的探索中:在第二场的开头,它暗示着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了,而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他的去世而悲伤时,那些最初的、平庸的时刻就是我们必须提及的。
就像我们对这位老人的匆匆一瞥一样,贯穿于《你那边几点》的互动是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只有自己的陪伴下,接触的时刻充满了意义,记忆将对过去的更深层次的感觉带到了未来。这种想要回忆过去的渴望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给一切都注入了意义,使无生命的生命充满活力,使空虚的空间充满活力,并扭曲了时间。
蔡明亮通过对事物的关注,让人们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寡妇(陆弈静 饰)试图通过对家居用品施咒,给丈夫做他最喜欢的饭菜,关上窗户,在奇怪的时间吃饭和睡觉来适应「他的时间」,以此来找回丈夫的灵魂。
虽然从来没有显示,「他的时间」——由厨房里停止的时钟建立起来——可能是由儿子小康(李康生 饰)设定的。他是卖表的,我们早些时候看到过他为了纪念前往巴黎的女孩湘琪(陈湘琪饰),在卧室里把时钟调到「巴黎时间」,他之前把自己能显示两地时间的手表卖给了这个女孩。
但是儿子从来没有纠正他的母亲,蔡明亮也没有定义哪个时钟的时间是巴黎的,哪个又是台北的:他们都在自己的时间里,共处于一个空间,却在不同的轨道,实时屈从于跨越空白的空间,与已亡人回到同步的节奏与时间。
起初,小康很宽容,但他对母亲古怪而绝望的行为感到厌倦,并试图阻止她。但他做不到,除了袖手旁观,他也不能提供任何安慰。她确信死者会复活,并在49天内禁止杀害任何生物。儿子在厨房里抓到一只蟑螂,然后把它丢进鱼缸里,蟑螂立刻就被滑稽地吃掉了。
没过多久,母亲猜想她丈夫游荡的灵魂实际上是在他们的白色大鲤鱼的肚子里游来游去。与鱼面对面,水淹没了她的眼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
在她的悲伤中,她失去理智,变得感伤可怜,她继续令人心碎、动人地说话。「你是来看我的吗?」她问,表达了被遗弃后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但愿,仿佛这样会使一切变得更好,更容易,或不那么孤独——但愿逝者能看到我们的悲伤。对他,对鱼,对我们,对她自己,她吐露道:「这真是太难了。」
小康的行为也很古怪,他把自己的悲伤转移到了对赴巴黎的湘琪的痴迷上。尽管他对母亲依靠咒语接近亡人的做法不屑一顾,但他对女孩的痴迷与这样的观念不无关系,即从服丧的人手中拿走手表等物品会带来厄运。(他把这句话转告湘琪,最后才心软,把手表卖给她;为了减轻他的恐惧,她声称不相信运气:「我是基督徒。」)
通过与她保持时间一致,并试图使台北的时间与巴黎的时间一致——通过越来越多地调拨公共时钟,他被与她在一起和保护她的愿望所感动。父亲永远不在了,母亲不在家吃午饭,他只有同情和悲伤陪伴着自己,即使不是那么强烈。
而湘琪则永远活在一个暂时存在的外国旅行者的身份里,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在变动,总是在自己的脑海里。她有显示两地时间的表,可以让她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却永远不能完全去任何地方。一个陌生人大胆地看着她,起初得到了回应,然后又被拒绝。一日三餐既平常又不寻常地充满焦虑。
她请求帮助,但当别人给予她帮助时,她对这种慷慨感到厌倦。独自旅行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喜欢自己的同伴;在另一个层面上,旅行拓宽了对联系的探索;在各个层面上,一个人会变得非常孤独,渴望与另一个人在一起。
蔡明亮在这里的观察是完美的、详细的、具体的,但又具有标志性意义。像这样的与世隔绝,像一个沉默的旅行者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城市里,有一种特定的声音,而《你那边几点》说了出来。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蔡明亮没有配乐,他让人们注意到不同空间的环境噪音,以及身体独处时发出的试探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的声音。在这个女孩所经过的城市空间里,寂静如同洞穴一般,而声音,如楼上酒店房间里的砰砰声,或鞋跟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咔哒声,都被放大并具有威胁性。
母亲在家里与心爱之人的照片甜蜜地约会(及最终的自慰),这个时候的她愈加悲伤,与此同时,两个年轻人开始对抗他们的隔离状态,并尝试与其他人接触;小康与一个妓女待在他的车里,而湘琪与一个同样身处异国的中国女人待在床上。
他们刚刚让彼此的联系逝去得太快,却各自坚持得太久、太牢固,在只能提供短暂安慰的地方寻找陪伴。蔡明亮将他们日益恶化的状况描述为:男孩失去了他的货物,女孩失去了她的财产。他们睡得很沉,早上肯定会更痛苦。
然后,在凝视了那么长时间消失的面孔之后,面孔出现了。当小女孩在杜伊勒里宫灰暗的晨曦中孤独入眠时,一个我们电影爱好者熟悉的面孔出现了,她从倒影池中取回了她那漂泊的手提箱。
巴黎时间毕竟是「他的时间」。这是电影人送的礼物,慷慨而神圣的礼物。在现实世界中,疲倦的人无法休息,甚至连《你那边几点》中三个孤独的主角也无法休息。但在把幸运的观众从他的世界中、他的可爱的、亲切的人性咒语中释放出来之前,蔡明亮跨越时区,跨越语言障碍,很可能在未来,提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