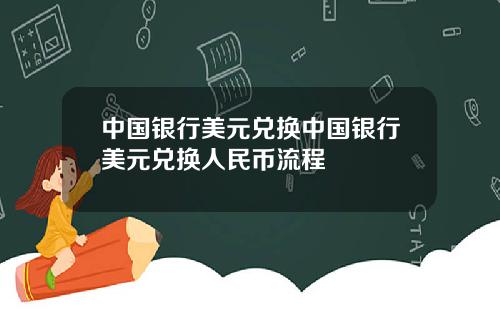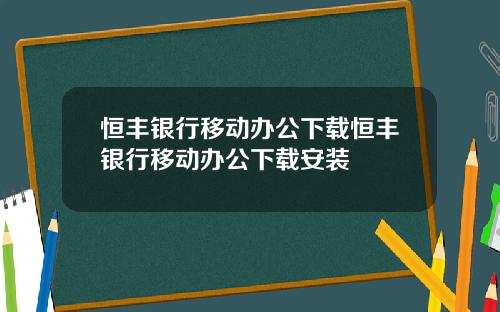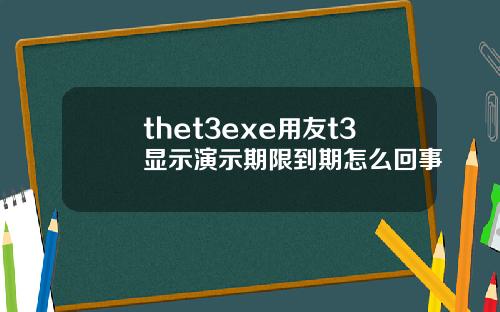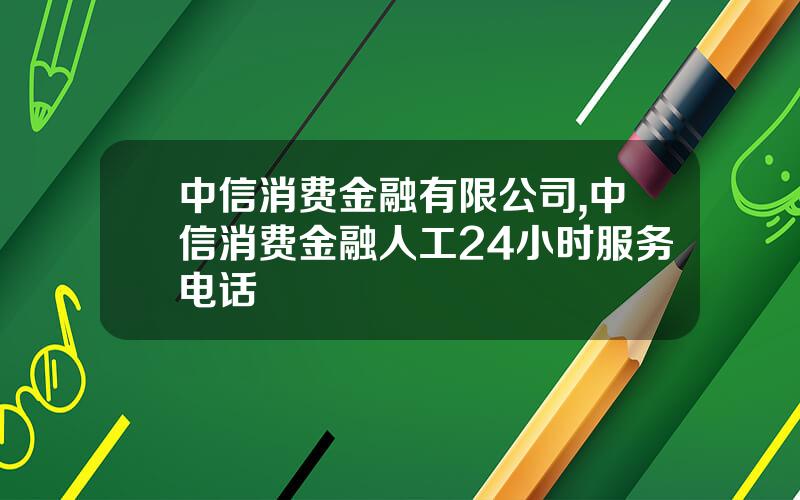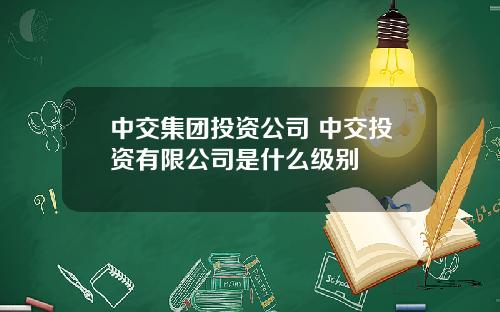一、渔趣
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春,我从芜湖师专中文系毕业,分配在青弋江边古镇西河中学教书。
西河江清沙白,盛产一种喊做“棉花条子”的小鱼。此鱼体狭长,圆滚滚的,大小如一根稍细的胡萝卜,鳞片上有迷彩麻点,头骨隆起,嘴前突,便于在沙里啄食。早年手摇纺车纺线,得先将棉花处理成手指粗细的“棉花条子”,好抓在手里一段段续接。许多人相信,这种被借形喊做“棉花条子”的小鱼,专在沙里寻找黄灿灿的金箔吃。有月亮的晚上,金箔反光,它们成群结队跑到浅水处觅食嬉乐,将水面弄得银鳞万点,当然也就很容易被粘挂在渔人的丝网眼里。此鱼几乎无刺,以文火煎烤成焦黄色,下调料加姜蒜焖出油来,入口香软,回味鲜绵。当地人惯常以之炖糟,味道真是呱呱叫,鱼盛在白瓷盆子里,在饭锅头蒸出,褐黄鱼体上,粘满白生生的被油脂浸透的糟粒,尝一口,又甜又咸的鲜嫩中溢满酒的醇香,真是风味别致。若是盐腌后再裹上面粉炸酥,和骨吞渣,香脆无比。“棉花条子”又称“蜡烛鱼”,据称若在体内插上一根捻线,可以当油灯照明。盖因其体多油脂,肉极度细嫩,才有如此非同寻常的美味。
楝树开花、青豆鼓荚的初夏,我常在早上踏着露水下到河边,寻夜渔的小船专买清一色的“棉花条子”。那是一种低平地贴着水的方头小船,头天傍晚就开始捕鱼,多是一双夫妻,有时是一对父子或兄弟,一人坐船头弄网,一人坐船尾划桨。桨行船行,桨住船止,指东打西,收网起网,配合极是默契。捕到了鱼,或养在船前一个隔舱的水中,或装进篓里,浸入水中悬于船后梢。到了早上就把船停在靠近渡口的沙滩边,有人来买鱼,就拎起竹篓,或拿一捞网去前舱里兜抄,抄得鱼劈里叭啦直跳,水花四溅。“棉花条子”这种鱼总是出水就死,当然享受不到竹篓或水舱的待遇,就搁在竹篮里,任你挑选。那些渔船,都有着陈年暮岁的色调,免不了这里渗那里漏的,总是当家的渔人弓着脊背拿一个硕大的蚌壳往外舀水。你挑挑捡捡弄好了,他才望一眼你,慢腾腾停下手来给你称秤,报账,收钱。
说到江南水泽中的鱼,我是知根知底见识不谓不多,唯这“棉花条子”学名是什么却无从得知。青弋江里还有一种放大版的“棉花条子”,七八两至斤把重一条,通体暗黄,着芦花斑点,我们喊作“鸡头”。但这“鸡头”不独多细刺,也少腴嫩,味道差远了。
夏天晚饭吃得早,就有许多人去看起拦河罾。拦河罾是在河道里安置的一张特大的网,有半个篮球场大。岸边栽着两根高高的毛竹撑杆,杆顶上有滑轮,升降绳穿过吊在撑杆上的滑轮与绞盘连接。梅天大水过后,有些地方加固的草包一个个堵在那还没有清除掉。站在高高的堤埂上,清凉的水腥气扑面而来,河里有几条渔船,一些船民在堤边建了些矮小的房子,水都退到房子下边去了,但涨水的印迹却清晰地留在窗台上。罾网起水时,可以听到网里鱼窜的扑楞声。西下的残阳照射过来,一些网眼里银亮亮地晃闪,被嵌住的小鱼——鳑鮍、餐条子多是给挂在网眼上。运气好的时候,碰上过路的鱼队伍,一网出水,能捞起一两百斤呢,河鳗粗得像胳膊,大草鱼有几十斤重,胖头鱼的鱼头比一个小坛子还大。
有趣的是,在拦河罾的上下游不远处,还有搬小罾网的。这种小罾网只有四五米见方,用两根交叉细竹竿对角绷起,有一根绳子直接拴在网架上,守株待兔似的等上一会儿,用力拉起绳子,罾网就出水。有时候很有收获,网心里有鱼儿乱跳,有时候却什么都没有。
二、鱼鹰
西河放鱼鹰的人,都住在离镇尾还有一小段路的圩埂内坡,要找他们很容易,只要闻到哪处散出鱼腥味特别强烈,直冲脑顶门,就是。
冬天里,一只只鱼鹰被主人拎着脖子提出来放到渔棚外竹竿上,或在树杈上,让它们撑开两翼晒太阳,且带梳理羽毛。然后就把从打撒网的渔户那里买来的小鱼小鳅拿出来喂,每抛出一条,鱼鹰都能准确接住,扬起长长的脖子一吞而下。它们在竹竿上立成一排,碧绿的眼里射出寒凉的光,有时会“咕咕”叫着闹摩擦纠纷,或是歪侧脑袋打量走近身边的人,然后“咕啾”一声拉下一泡白石灰水一样的便溺。
鱼鹰又被喊成“鱼老鸹子”,它们的学名叫鸬鹚,在自然的环境里是很善于飞翔的,剪掉了翅羽后,被人豢养,成了活的捕鱼工具。鱼鹰分生鹰子和熟鹰子两种,前者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学徒级鹰子,也有是天性慵懒脾气不好的,得下功夫调教,后者则全是三岁以上劳模级鹰子。熟鹰子能在浑水里睁眼,在湍急的水流里辨识鱼路,能捕到大鱼。
陶老二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我们在一起喝过酒。他告诉我,西河鱼鹰是品牌,全国有名,考核指标是独自能从水底拖上来十几两十斤重大家伙。陶家数代驯鹰,家里现存十一只鹰,有五只就要下蛋了。一只鹰冬春季节约能产下40枚蛋,由老母鸡代孵,也跟鸡一样24天小雏出壳。雏鹰自小要熬,手段种种,直到熬熟。
天气转暖,陶老二就担着鹰子艇下到圩堤脚底河里捕鱼。他没穿牛皮罩衣,只在腰间扎了一条防水黑橡胶围裙,两腿也绑了胶皮。鹰子艇是一对一人来长两头尖翘的连体艇,两边隔着一尺多宽的空隙,人钻到中间可以挑起来走路,放到水里,叉开双腿一脚踏住一边,能稳稳地站上面用竹竿撑行。挑行时,这些歇了长时的鱼鹰分立在艇两边木架上,一个个都好像很兴奋,不停地鼓嗉子,扇翅膀,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
看鱼鹰捕鱼,是快乐的事情。陶老二把鱼鹰赶下水,篙子一摆,鱼鹰一齐扎进水底。过一会子,这里冒一只出来,那里冒一只出来,口里衔着亮闪闪的鱼,向艇边游来。陶老二伸出竹篙一拖,挂住鱼鹰脚上的一个线卡,收回竹篙,将鱼鹰抓到手里,就势扒开鹰口,朝着艇舱一摁,鱼鹰嘴里的鱼就落下,连同已吞入喉中的鱼都全吐了出来。被重新扔入水中的鱼鹰,翻身又一个猛子潜下水……陶老二左顾右盼观察四周水域,顺流而下且捕且赶。
捕鱼的高潮,是下游的鱼鹰兜抄上来了,几条鹰子艇呈合围之势。陶老二脚踏鹰子艇,剧烈晃摇,嘴里“哦嘘”“哦嘘”的喊着,挥动竹竿击打水面“啪啪”作响。水浪叠起,鱼鹰仿佛大受鼓舞,激情高涨,纷纷窜跃着猛往水里扎,上下穿梭,忙得不亦乐乎。水底的鱼藏不住了,慌不择路拼命逃窜,有些小鱼急得跳出水面,能看到鱼鹰伸着长脖子在水下追撵的黑乎乎身影。眨眼工夫,一只嘴里叼着鱼的鱼鹰浮出水面,接着又是一只……有时两三只鱼鹰合抬一条大家伙,任凭水中如何波翻浪激,它们那尖钩一样的利喙死死叼紧鱼嘴或鱼眼不松口!
三、白兰花
同许多江南古镇一样,黛瓦粉墙、廊檐交错的西河也是诗情画意的性灵之乡,居民多喜欢品茗聊天,去户外散步踏青。雕窗屏风的人家,条几上摆花瓶,壁上挂字画自不必说,湿漉漉的天井和深墙院落长满虎耳草和凤尾蕨,四周摆有花草假山和鱼缸,此所谓“构园无格,借景有因”。
学校近旁住有一位姓丁的木匠,此人虽短身陋貌却极是灵慧,种花养鱼扎风筝制盆景,门门俱精,他的两儿一女皆是我的学生,个个成绩优异。从谷雨到立夏前后的每天下晚,我都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在那个蜂吟蝶飞的小园里消磨宜人的时光,陪着莳草弄花的丁木匠穷聊海吹。丁木匠教会了我区分芍药和牡丹这两姐妹,牡丹先开,芍药花期要晚半月。芍药归草本,地面茎杆每年新生,光鲜稚嫩,一掐就断;而牡丹的茎杆是小木棍,虽细,却生长多年很显沧桑。芍药叶完整,颜墨绿;牡丹叶有裂,状似鸭脚,背面有粉……
丁木匠也像镇上许多人家一样,有两口很大很雅致的宜兴紫砂缸,里面栽着一人高的白兰花树。冬天严寒,就把花缸搬进室内装饰客厅。一年中,他的白兰花树共有三次吐馥扬芬,第一次在清明到谷雨,第二次在梅雨期,第三次在立秋前后。前前后后,花期长达小半年,以草木葳蕤的初夏开花最盛。
那些年,夏天总是来得早。杏子黄熟,江南入梅之后,小镇的空气里便有了夏天的味道。但天气却总是湿漉漉的,时阴时晴。
在街头走着走着,就有微风吹送幽香过来……隔着小院或是转角巷子口,看见人家屋檐下的白兰花开了。那些寸来长的花儿,颜色是清一色超凡脱俗的白,像玉一般温润,给人几分乖巧的凉意。虽是一身的淡雅与素净,却是花香也热烈,浓郁也持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起那类枕着“银床梦醒香何处,只在钗横髻发边”诗句。
一个身姿绰约的长发女孩被花香吸引,停下了袅娜脚步,从绿叶缝间拣出一朵两朵白兰花,先放鼻下嗅过,再把花朵小心藏入丰凸的胸襟下……被一股动人的清香缭绕着,她那张秀丽的瓜子型脸,便多了一种江南女子温柔娟好的风情。
氤氲不肯去,还来阶上香。江南五月天气里,最自然最诗意的饰物,也许就属白兰花了。
白兰花是最经典的小镇之花,它枝干秀丽,树姿优美,长椭圆形的叶大如手掌,灵润光泽,清翠碧绿。细长的嫩绿色花蕾是从叶腋间抽出的,犹似一只只翡翠簪头,玲珑可爱。待到花蕾日渐长大,绽开裂口,露出内里的象牙白,在某一个晨间或傍晚静悄悄开放时,这寻常的花朵竟有着脱俗的美,如处子低首,娇羞不可名状。尤其是在月洗高梧、桐荫冉冉的夜色里,微风起时,清新的叶子恬淡怡然地舒展摇晃,掩映得那些白瓣细长的花儿,分外有一种骨骼清奇的薄凉之感,而浓郁的香味,更是有着销人魂魄的风情。
摘下来的白兰花,最好的保鲜法子,就是用湿毛巾包起来,放一夜,照样水灵灵的,幽香四溢。
永远的白兰花,总是飘在古镇悠悠的南风里,总是袅娜绰约着那清丽的身影……
四、馄饨担子
日常里我们都把小馄饨喊做“饺子”,下一碗“饺子”就是下一碗小馄饨。
那时西河特别好吃的小馄饨,大多是在担子上下出来的。担子一头,下面摞着木柴棒,上面炉子上置一口钢精锅,锅里是待开或已开的沸水。另一头是个简易柜,里面盛有碗勺跟铁丝爪篱,上面放一长方盘子,里面摆着包好的混饨和馄饨皮、肉馅、葱、胡椒、猪油、酱油、醋之类。担子每天都是停在一个固定处所,像菜场旁、旱桥头或是码头边,早上挑出来,晚上担回家。若是逢上哪里唱戏或是出灯,就去赶场子。平衡功夫好的人,挑着这样的担子,不要手扶,只管拿着两块竹片边走边敲打,嗒,嗒,嗒嘀嗒……想吃馄饨,就会闻声而来。
冬夜澡堂子外昏黄的路灯下,担子一头柴火红红,锅里热汽腾腾……旁有小桌小凳,有人过来,招呼一声,或是抓一把成品下到锅里,或是现包现下。包馄饨手法极快,左手托皮子,右手小竹棒挑点肉糜往上一抹,手指捏着一窝,扔到一旁。再看这边锅里,水滚,馄饨上浮下沉,反复几次,皮薄得能看到馅心的一面朝上,必熟无疑。几分钟光景,一大碗热气腾腾、汤波荡漾的馄饨就下好端上来。这种皮子薄到透明的小馄饨,只须嘬吸,入口即化。那香气,那暖暖的感觉,总能诱惑夜归的人。
小馄饨下得最好吃的师傅大老王,住在一幢带天井的老旧大屋里。有时阴雨天不出摊,我就拿一个大号搪瓷缸穿堂入户去他家中等候。去早了,看他剁馅打皮子,也就知道其中是很有讲究的。馅须用当天宰杀的猪前腿夹缝肉,八分瘦两分肥连筋带绊的,若是纯精的后腿肉反而不好。个头很高的王师傅,躬着身,双手各持一把刀上下翻飞,直把一小钵子肉剁成肉末。再用一根圆筒状的棰棒敲打,肉打得越久,越熟,越打越膨胀。打到最后,喷起的肉茸会起丝,极“粘”包馄饨的竹棒。擀面皮要入碱,分量掌握不好跑了碱,在猛火沸汤里一煮一冲,馄饨就会破皮。擀面时加入鸡蛋,能擀出最佳效果,所谓“薄如纸,软如绸,拉有弹性,吃有韧劲”,就是这效果。这边,他老婆把擀好的皮子垛起来,拿刀切成二寸见方若茶干子大小,一般十张皮放秤上称一下正好一两,再裹进一两馅心,便是一客小馄饨。
小馄饨不似水饺和面条,不是用来撑肚子的。吃这种小馄饨,纯粹就为了味道,为了享受那碗热气腾腾的鲜汤——不求吃饱,只求口味。小馄饨要的是皮薄,肉馅不能多,多了就荒腔走调不是那味儿。小馄饨汤水甚为重要,先在碗里放好盐、酱油、猪油和焦褐的油渣,用开水冲兑,以免汤水混浊,再用笊篱捞入小馄饨。十个似穿了柔软蝉衣的小馄饨在碗里还轻轻的打着转,一撮嫩绿的小葱撒在上面散开来很是养眼好看,用汤匙稍稍搅动,但见一片片羽衣缥缈,裹一团团轻红,上下沉浮飘摇……舀上一个吹一吹,牙齿轻轻一叩,满口的汁水,真上香鲜透骨!
我是最在意吃夜晚的小馄饨,一碗下肚,五内温热,正好一路吟哦着走回宿舍。有雨的秋夜,雨打芭蕉,风灯飘摇,若是听到青石板小巷传来一串幽沉足音,该会唤起多少别样的心情意绪呵!
五、铁匠铺子
那时的西河有六七家铁匠铺子,整日里丁丁当当,数下街头董师傅那里传出的声响最大。
夏天,铺子檐口撑出一块灰白的布帘,下面一张低矮的木案上,整齐地摆着锄头、镰刀、粪耙、铁叉等农具和菜刀、火钳、链条、老式肉钩等生活用具。进了屋,发现里面别有洞天,高大宽敞,像个仓库样子。屋顶有亮瓦,后间塌垮的墙头露着一大片缺口,阳光循着声响照进来,风也能轻易吹入。迎门靠墙位置,有一个半圆带烟囱的打铁炉,炉中的炭火烧得很旺,墙壁早被熏黑,墙角地上摆着一大堆铁件,一边还放了个装满水的水桶。炉子前有两人:一个持钳把铁块,一个拉风箱,风箱停下来就拿起大锤锤打。
董师傅壮实,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一只左眼有点疤,炭火星溅的,身上系的深色围裙上尽是斑斑点点烫洞,脚上的鞋也有许多烫洞。他的手显得特别大而有力,打铁的架势有板有眼,借用旁边高温的炉火来形容,叫“炉火纯青”。那一个瘦身脸带稚气的,是徒弟。
师傅左手握着一把黑铁钳,熟练地夹起一块铁棒,埋入炉炭火中烧,徒弟拉着风箱呼达呼达地鼓风。待铁棒烧红后,将其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右手里那只三斤重的小锤“丁”一声敲在铁砧子“耳朵”上,仿佛是试敲,第二锤才落在红铁棒上。伺候在旁的徒弟得了小锤指令,立即抡起大锤砸下……“丁当丁!”“丁当!丁当!”“丁当丁!”“丁当!丁当!”“叮叮当——叮叮当!”小锤落哪里,大锤也精准地砸在哪里,你一下我一下,在四溅的火星里砸下一片金属的嘹亮。打铁有“锤语”,小锤敲得急,大锤也砸得急,小锤敲得慢,大锤就跟着慢。单击与连击,轻击与重击,均由“锤语”引导;若是小锤再一次敲打在铁砧“耳朵”上,大锤就要停下来。
他们将铁棒打出一个尖头,然后折弯,铁棒的颜色重又暗下来,再埋入炽炭火里,鼓风窜火烧红,取出再打。最终,夹起成型的铁件插入淬火的水桶里,滋的一声,一溜青烟冒起……这样,铁件才算真正坚硬了。徒弟给炉子添了一小锹碎煤,重新放上了两根粗铁棒,又拉动风箱,蓝色的火苗呼拉一下四散升起,要冲出来的样子。
所谓趁热打铁,打铁时火候的掌握很重要,要是温度不够或是火力已降下来,铁件颜色不是那么红亮,还在锤打,铁件被打裂了,修补麻烦,很难再敲到一起去。老话说人生有三大苦:打铁、拉锯、磨豆腐。打铁排第一,说明确实辛苦。打铁是力气活,师徒俩配合,不用讲一句话就心领神会,只管闷头去打,精炼而简约。
他们铺子外的街道格外狭窄幽长,最窄处仅容四五人擦身过,抬头只见一线天。冬天早上挑担子卖柴草的多,常给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给挤下来站在沉降式的门阶上,师徒俩不为所动,大锤小锤依然起落有致响着。反正一时出不去,有人会绕过铁匠砧子一直往里走,走到后间塌垮墙头旁那个大窗前,贴紧脸朝下看……哦呀,下面笔陡,都是大条石直驳上来如悬崖绝壁!
西河下街头都是这般场景,梅雨天山洪下泄,迎流顶冲,正对水头,不如此对付不行。
和我关系较好的铁匠是老七,老七姓李,大我两岁,人喊七斤子,他的弟弟叫八斤子,常在学校操场打篮球和我混熟了,两兄弟的茅草屋就搭在西河中学东边围墙外。我刚分配到中学时没地方住,曾与两兄弟在一张床上捣了多晚上腿。老七有次相亲,我脱了白衬衫给他换上,手表也捋给他戴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没相成?再后来,八斤子去了宣城,老七独自一人留在西河打铁终老。
六、篾匠
1980年3月,我当了快一月老师,学校终于给我租了一处住宿,就是姚篾匠家西半间屋,也是茅草房,但整洁明亮。
姚篾匠高个、善良,讲一口巢湖话,子女在湾沚,老伴料理家务,自己整天都在干活。篾匠不像木匠,使用的工具不多,无非就是些锯子、弯刀、凿子、钻子、度篾齿等。度篾齿这东西有些特别,铁打的,像小刀一样,安上一个木柄,一面有一道特制的小槽,它插在任何地方,柔软的竹篾都能从小槽中穿过去。
看姚篾匠剖大毛竹很是带劲。一根碗口粗的毛竹,一头斜抵在屋壁角,一头搁在肩上,用锋利的篾刀在竹蔸子这头开个口子,双手将刀往前用力一推,大碗般粗的毛竹,啪地一声脆响,裂开了好几节。然后,顺着刀势使劲往下推,身子弓下又直起,直起又弓下,竹子一路噼啪噼啪炸响,节节裂开。要是竹节太硬,刀给夹在竹子中间,动弹不得,姚篾匠就单脚踏住下片,用一双铁钳似的大手抓住裂开口子的上片,鼓起双眼,用力一抖一掰,随着啪啪啪一串爆响,那根毛竹一裂到底,真叫势如破竹!
附着在竹子内层的白色竹衣,轻轻飘动着,我有时走过去小心揭下来,拿回房间平整地压在书页中,留着日后送给一个吹笛子的朋友做笛膜用。
篾匠干的是精细活,全凭手上功夫。一根偌长的竹子,被一剖再剖,劈片削簧,篾片再剖成篾条。篾条的宽度,六条并列,正好一寸。然后,将刮刀固定在长凳上,拇指按住篾条在刀口上刮……一根篾条,起码要在刮刀与拇指的中间哧啦哧啦地拉上四次,这叫“四道”。厚了不匀,薄了不牢,这全凭手指的感悟与把握。
要是剖那种手指粗的小水竹就容易得多,姚篾匠用锋利的弯刀按住粗头,用力挤开一道口子,然后,刀上带着腕力一搅,“啪”一声脆响,就裂开了。再用力一抖,噼哩啪啦一串悦耳的响,一根竹子就成两爿了。竹子劈成较细的篾后,外面的一层叫“青篾”,最结实。不带表皮的篾就叫“黄篾”, 黄篾又分为头黄和二黄,韧性虽比不上青篾,但它是编箩筐、摊簟的主要材料。由于需要量大,箩筐和摊簟篾都由毛竹剖成,唯得劲部位一定要用上青篾。像经常沾水的篮子、筲箕之类,就得用本地的水竹篾来编织。水竹不怕水淹,特别柔韧,耐腐蚀,它们多产于青弋江上游的大河马一带,珩琅山脚底往西南也有连片竹林。
编竹器要眼快手快,全身各部分都要配合。姚篾匠抱着一只竹器两手翻花编织,时不时要用嘴迅速地把竹篾扯开,嘴就是他的第三只手。看他编竹篮,先起一个盘子,八支竹篾为一组,一手收拢竹篾条,一手灵巧地让另一支新插入的篾条在篮子的竹孔里穿梭,手上动作快起来,犹如杂耍表演,青色、黄色的竹篾上下飞舞,飞短流长,真让你眼花缭乱。
打簟子是真正的细致活。姚篾匠蹲在地上,先编出蒲团般大的一片,然后就一屁股坐下来,悄然编织开去。打簟子的篾都是用老水竹剖出来的,按竹篾的宽窄层次而定簟的优劣,薄窄的青篾和二黄篾较好。新簟子编出来,要用破布鞋粘泥或细砂认真打磨,磨光每片篾的棱角和细刺,再放进澡堂收工后的热水里烫煮,以后篾片有韧性不脆。姚篾匠有一套按竹篾宽窄打制的平口铁“引针”,墙上一年到头总是挂着好多个长篾绕成的圈环。有人送来了破损的簟子,扫一眼簟子的篾宽,从墙上摘下相应的篾圈,立刻就给人家修补。
我在姚篾匠家住了一年零两个月,学校给腾出一间宿舍就搬走了。时已初夏,搬离那天,姚篾匠送给我一卷四尺宽竹簟,全青篾的,很珍贵……我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编成的。
七、弹花匠
“檀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弹花匠,亦有称弹花郎的。
我常看一位姓孙的弹棉花师傅干活,他的店面在澡堂子上去那条巷子口,也算临街,但却下陷很深――由于古镇是傍堤筑舍,为防洪计,圩堤逐年加土,故街面亦随之壅积增高,形成两边店铺人家的窗户与青石板街面平齐的奇特局面。
有着很深抬头纹的孙师傅常年穿一件蓝布褂子,肩膀上背弓的那一侧补着一大块黑色的补丁,头戴一个蓝布套头帽,下面捂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弹棉花时,花絮尘埃像“雪花”一样满天飘飞,从头套到眼睫毛,连同下身系的围裙上沾的都是白色的花絮。尽管年纪不算太大,孙师傅摘了套帽头上仍是白的,这是真白。他把一张大木弓背到身上,木弓用绳子系在背后腰间的竹竿顶头,这样可以减轻不少弓的重力。你看他一手操控着木弓,另一只手握一个如哑铃样式的木榔头有节律的敲击弓弦,嘭!嘭!嘭——嘭!嘭——嘭!嘭!嘭……声音奇特的响亮。牛筋做成的弓弦,像弹橡皮筋样的震荡,使棉花纤维被拉开,蓬松并飞扬。弓弦上常挂着棉丝影响弹性,于是木榔头还得“啪”“啪”敲打木弓架,以便甩震掉棉丝让弓弦深入到棉团中去弹拉扯撕。在嘭嘭的声响里,棉花慢慢蓬松,如风卷白云般堆积起来。
弹花匠弹的大都是棉胎,也有的是垫被棉褥。姑娘要出嫁,总得弹上几床新被褥,这样的被子,几乎是要将自己一生盖到头,就像那时的婚姻,山长水远且平阔。还有,平常过日子人家,旧被子压硬梆了,一点不暖和,也得乓乓松,翻翻新。只是这旧棉重弹要多两道工序,首先得除掉表面烂黑的旧纱,然后卷成捆,由徒弟双手抱着反复往一个满布钉子的铲头上拉扯撕松,再铺散开来用弓弹。
随着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起落,最后把一堆棉花弄成一条平平整整的被褥。若是送到裁缝那里做棉衣的絮棉,份量就不大,弹好后卷起来,用报纸包了,外面再扎一道细绳。刚弹出的新棉,洁白,蓬松,用手摸上去特别温软。
我站在高高的街面窗户口朝下看孙师傅嘭、嘭、嘭——嘭、嘭、嘭地敲击弓弦,他的身子单薄的徒弟就站在一旁,垂手而立,仿佛是在欣赏师傅魔术般的表演。其实徒弟是在等候着打下手,帮师傅为棉胎“上线”。“上线”又叫“网纱”,也有喊做“找面子”的,必须由两人做对手才能完成。他们先根据定好的棉被尺寸,布好底部的纱线,然后往上面铺棉花。将棉花均匀放置、摊平后,再用一个光滑的大白果树木盘一遍遍按压,捺实。木盘很厚重,像个大锅盖,又像盾牌,背面凹进,装有一根木档做抓手。
看他俩放骨线亦有趣,先放出一“米”字做定位——放骨线的竹竿梢上是有洞眼的,棉纱从眼里像穿针一般穿过。放好“米”字定位后,竹竿顶部勾着纱线腾来挪去,似蜻蜓点水,又似蜘蛛织网罗云……细纱随着师傅手里的竹竿在飞舞,徒弟手臂探过来弯下去地在对面接纱,当五指都套上纱时,便一起按伏在弹好的棉絮上,纵横布成网状。远远看去,师徒俩配合有致,“上线”的动作又快又利索。纱网好后,再用那只厚重的圆木盘将纱按进棉絮里,反复多次压磨,使之平贴,牢固。从弹、拼到拉线、磨平,这时一床棉胎才算完工。
所有的弹花匠都喜爱弹结婚用的被胎,不但能拿到工钱,还能拿到红包喜钱。只是用作嫁妆的被胎的纱,须显示出喜气,除了正常网纱外,还要用红绿两色纱缠绕出两个鲜艳的“红双喜”。手艺很好的孙师傅,往往还会网上龙凤或鸳鸯图案,以示喜上加喜。如果是老人睡的棉被胎,则铺出一个大大的“寿”字或是“福”字。腊月年底,是手艺匠人最忙的时候,夜晚从街上走过,常见孙师傅他们的身影晃动在昏灯的光晕里。
若当一轮圆月升起——抑或是一弯古典的幽月转过高高马头墙耸成的巷口,照着那些翘角飞檐,照着那些小巧的庭院和优雅的月洞门,清风拂过,嘭嘭声响,传到耳底尽是往日的悠长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