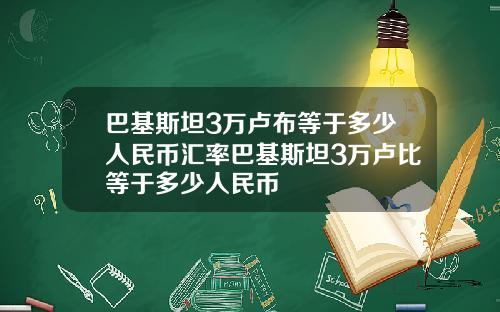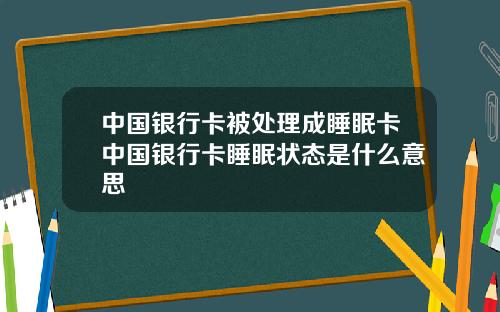上海与印度一样,具备相当程度的广阔与神性。
你能见到无所不在的牛,也能见识到无所不能的神牛。
一些刚出道的明星,在上海举办演唱会,可能会有意无意采用一种话术。
“对不起大家辛苦了,你们甚至买黄牛票来看我,我很感动,但希望以后不要找黄牛,谢谢。”
其实每人都知道,不找黄牛,可能没法给另一半一段共同的回忆。
在一些时间紧迫又缺乏渠道的人看来,黄牛可以提供的服务价值和价格相比不值一提,它们是线下文娱的反哺者,是没有需求就创造渠道的过路财神。
黄牛从词义上,代表着某种“勤恳”。
“开票三分钟就售罄”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去了现场,你才发现,靠近过道和最后几排的位置,总是有无所事事的大爷大妈在点评明星的穿着,甚至有大量的座位还空着。
你不解,你沉思,本质上两情相悦的生意,但操作手法令人迷惑。
常规演出出票率达到60%-70%,能保证明星、经纪、票务和黄牛都会微笑。
剩下的都算额外收益,一些在二手平台临近演出还未售出的票,可能都免费送给了周边的群众演员,注意,来不来还得看他们的档期是否充裕。
去年上海天文馆开馆,短时间内票务后台就涌进了2000多个“异常帐号”抢票。
天文馆不得不升级了防护技术,同时在线下进行人证比对、真人验证的方式进行安全检测。
新交规实施之前,驾照买分卖分在“黑市”价格是12分4000元。
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外省的牌照,只要是在上海地区违章扣分的,黄牛都可以处理。
分是如此,车牌也可以。
14年时,浦东新区未上牌的新车车主,必须在特定地点先购买“标书”,然后才能在网上参加拍牌。
上海的拍牌难度可想而知,人群中来回穿梭的黄牛,可提供“代拍”服务,价格从5000元到1.1万元不等。
“代拍”的价格只是支付给“黄牛们”的一笔劳务费,拍到牌照后,你还得为一块牌照支付7万余元的“牌照钱”。
“就这还是时价,14点后的价格更高,因为黄牛要喝下午茶,不劳动的。”
“春运那会返程,无论去哪票都不好买,当地的黄牛在我排队时,问我要不要走‘绿色通道’,只要300块,我跟他走到进站口旁边的人口检票口,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爷朝站内扔过去一个遗像,喊了句‘我*,别挤我的小芳’,然后趁工作人员过去捡拾的时候,一把把我推了过去...”
“同时,同地,我还见过扔钱包和假肢的。”
就地取材,来源生活,黄牛不生产票,他们只是对‘借力’这个词充满深邃的见解。”
甚至,同样的操作,还出现了人传人的症状。
黄牛在狱外学不全的法律条文,可能在狱中会有切身的体会。
上次一同学去迪士尼,有个黄牛问她需不需要免排队的服务,只要200块,她一想合适,就给人转过去了。
然后那黄牛竟然带她们插队,别人骂她们他还帮着还嘴,我同学在上边玩项目,这黄牛就在下边和人家对骂,六国语言,保证输出到位。
想上厕所了,前面排队的比玩项目的还多,也有厕所黄牛,50一次,一身怀绝技的大姐跑完女厕队伍最前端,假装接电话,先小声咕哝一句,然后高喊了声:“阿拉有艾滋怕侬模子?”然后换了种口音,“我告你,我早阳了”,周围瞬间没人,“我大三阳的!”,又换了种口音。
事后我同学回忆,“大姐说她是为了照顾听不懂话的乡下人。”
但由于人太多,很多黄牛也都十分珍爱生命,放弃了使用物理手段,改卖起了挤不死人的园区早餐。
“星可以再追,命只有一条”。
整治之前的上海,几乎每个景点、每个商场,甚至每个领域都有黄牛。
它们像这个城市的502万能胶,把一些不相干的蛋皮,强行拼合在一起,算冲突美学。
加油加气有油气牛,医院有挂号牛,银行办公积金或买理财有金牛,上海是东亚最富潜力的城市之一,满溢的人才、稀缺的资源、拥挤的流量,是黄牛成长的天然土壤。
拼车有黄牛,买数码有黄牛,就连买月饼和蝴蝶酥也有黄牛。
甚至,商场促销返券,小朋友升学也都有相应行业的黄牛,如果社会工程学能发放学位,这些黄牛人均博士。
黄牛是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会有工伤,每年被抓进去的和新出道的一样具有活力。
十年之后,再看《2012》,会觉得那是部搞笑电影。
如果最后登船仅仅靠的是财富,那么请找上海的黄牛,估计连诺亚方舟最后的船票都能给你弄来。
“以前的黄牛,就是典型的‘票贩子’,先囤票,再加价售卖,现在都用上高科技了。”
与黄牛相对的,是代拍行业,而当黄牛用上代拍,就好比是流氓会了武术,还能申领低保补助,让人无比懊恼。
“火车票都实名制,抢票的门道在于代拍,黄牛用你的身份信息,上抢票软件帮你抢。疫情期间,高价抢票费是乘火打劫,扰乱正常秩序,是非法的。”
图片来自 央视新闻 截图
在上海的方言语境中,惯用“党”字给社会现象分类,是一种认知概念系统,相当于现在的打标签。
“拆白党”是凭色相吃软饭的,“黄牛党”就是俗称的“票贩子”。这种行当在北京行话叫“拼缝儿的”,近年来上海方言还称“打桩模子”。
长期以来,黄牛总是和文艺领域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片来自 央视新闻 截图
“黄牛”一词,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彼时的上海已开埠80年,是亚洲的繁荣都会,被形容为“冒险者的天堂”,遍地黄金。于是,一些本地或外地的闲散人员,通过人海战术排队抢夺票源,然后再向公众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成为当时的地下经济之一。
由于票贩联群抢购票时,常如过江之鲫,又如黄牛在野,有蛮力、有方案也有秩序,故他们被称为“黄牛”。
京剧名角梅兰芳,在日本侵华期间蓄须明志,告别舞台,不为日本人演出。
他在1939年底于北京做最后演出时,当时一张票被远道过去的上海黄牛由两元炒上五十多元,创下了飞票纪录。
图为 梅兰芳
而粮票时期的倒买倒卖和投机倒把,反而不叫黄牛了,只称呼其为“倒票人”,因为实在是缺乏技术含量,完全凭借的就是渠道资源的稀缺,连“劳动”都算不上。
黄牛在某种程度来看,又是有品味的,他们懂文化产品的溢出价值,也懂名人的产出效应,更懂危机时刻人心的浮动与紧迫需求。
为了高额的利润,一些人选择了铤而走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以身试法身陷囹圄。
而真正的心安,也如同原野里的黄牛,不费心思地劳作过后,停下来遥望夕阳,回到那个人心朴素的故乡。